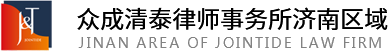内容摘要
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相剥离而独立设罪,表明立法者认同在金融诈骗罪中蕴含了一般诈骗行为所不具有的特质,对于这种特质的理解与把握实际上就成为准确适用金融诈骗罪的钥匙。在金融诈骗罪的适用上刑法的谦抑性应该得到更多地重视与更全面地体现。不同类型的诈骗罪对于欺诈程度的要求不尽相同,相较于一般类型的诈骗罪而言,金融诈骗罪在欺诈程度上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与标准。同时,金融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与把握上也与诈骗罪存在差异。
关键词:
金融诈骗罪 限缩适用 欺诈程度 非法占有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诈骗行为的规制,不仅包括一般类型的诈骗罪,还包括针对特殊领域的金融诈骗罪。从立法沿革来看,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诈骗罪,对于上述金融诈骗罪并没有涉及。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金融市场日渐活跃,金融行业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金融领域当中的诈骗犯罪也随之水涨船高。因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相应地规定了八类金融诈骗罪,从而形成了现行刑法所呈现的作为侵犯财产罪的诈骗罪与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金融诈骗罪相分离的立法体例。
金融诈骗罪原本属于诈骗罪,两者之间实质上是一种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因而人们在对特殊类型的金融诈骗罪进行理解与适用时,总是不自觉地以诈骗罪的思维模式与解释路径去诠释金融诈骗罪的内涵,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理解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偏差。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相剥离而独立设罪,表明立法者认同在金融诈骗罪中蕴含了一般诈骗行为所不具有的特质,对于这种特质的理解与把握实际上就成为准确适用金融诈骗罪的钥匙。因此,有必要探寻立法者设立金融诈骗罪的实质根据,把握金融领域的价值取向,进而反思我国目前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研究现状,准确把握本罪的适用范围。
一、金融诈骗罪立法目的之探寻
金融诈骗罪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犯罪群,其原因不仅在于本罪的适用领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更在于其背后体现了与诈骗罪所不同的价值关怀与目的追求。这使得金融诈骗罪具备了诈骗罪所不具有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恰恰成为其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犯罪的根本原因。
(一)金融领域价值取向之分析
理论上一般认为,金融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而来,兼具金融犯罪与财产犯罪的双重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i]]但是这种传统的见解实际上以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来思考21世纪的金融领域,以静态财产所有权的概念来把握动态的金融流转形式,结果势必南辕北辙而不得所求。因此,想要准确理解与把握金融诈骗罪的立法目的,就必须从更实质的层面去分析金融领域的价值取向,此乃打开金融诈骗罪之门的关键所在。虽然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都涉及到对财产权益的保护,但实际上两种犯罪关注的侧面并不相同。传统的财产犯罪多发生于生活领域,其更关注静态的财产安全,以所有权为本位构建自己的犯罪体系,因此对于刑法的介入程度要求较高。相反,金融诈骗罪发生于金融领域,而金融领域对于效率的追求远胜于安全的考量,风险与机遇并存乃金融行业之特性,由此决定了金融领域更重视动态的资金流转。常言道“富贵险中求”,金融效益的价值目标限制了刑法的介入程度,防止刑罚以效益损失换取交易安全,同时金融风险也抑制了刑法介入的力度,不得完全扼杀金融风险。[[ii]]这种价值取向有别于一般财产犯罪的全面保护原则,金融领域对于效率的重视决定了立法者在对金融诈骗罪进行惩治时,不得不采取一定的限缩态势,以防刑法的过度介入将会伤及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
(二)金融诈骗罪限缩适用之根据
有论者认为,从整体上说,金融诈骗罪实际上是比诈骗罪更为严重的犯罪,不管是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来考察,还是从刑法的规定方式来考虑,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因而,刑法规定金融诈骗罪并不是为了限制诈骗罪的处罚范围。[[iii]]对于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虽然法益侵犯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行为的严重程度,但实际上,行为的严重程度与是否予以重处之间并非是必然关系,刑罚的适用除了需要考量报应因素,还需兼顾预防效果。尤其涉及到特殊领域的刑法介入限度问题,更应该是综合权衡之后进而作出最终判断。金融领域的价值取向有别于日常生活,故而就金融诈骗罪的定位而言,笔者倾向于其意在限缩诈骗罪在金融领域的广泛适用。首先,从理论层面的分析来讲,即使在刑法典中没有规定金融诈骗罪,对于发生在金融领域中的诈骗犯罪行为依然可以通过适用诈骗罪予以惩治,正如即使不存在医疗事故罪这一针对特殊领域的过失犯罪,其行为方式仍然可以评价为“过失致人死亡”。而医疗事故罪的法定刑只有3年以下有期徒刑,过失致人死亡罪则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在特定领域设置特殊性罪名,其意图绝非扩张一般罪名的适用,而在于限制其适用范围的过分蔓延,否则这种“特殊规定”则没有价值,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其次,从入罪门槛的角度来看,就诈骗罪来说,根据司法解释,骗取公私财物3000—1万属于数额较大,而就金融诈骗罪而言,集资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0万以上,信用卡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标准为5000—5万。同样的数额较大,但在认定标准上却存在悬殊,由此可见,相较于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的入罪门槛更高,入罪要求更严,这充分体现了限缩诈骗罪在金融领域的适用。最后,从刑法修正的方向来看,《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分两次全面废除了金融领域犯罪的死刑规定,将一些金融犯罪的法定最高刑减档为无期徒刑。[[iv]]金融诈骗罪设置死刑一直以来就为学者所诟病,立法者通过修正案的形式降低对金融诈骗罪的刑罚配置,亦可视为限缩其适用之明证。
二、金融诈骗罪欺诈程度之分析
金融领域有自己的价值取向,金融行业有自己的目标追求,这使得对于金融领域的调整规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在金融诈骗罪的理解与把握上与诈骗罪存在很大区别,换言之,在金融诈骗罪的适用上刑法的谦抑性应该得到更多地重视与更全面地体现。秉承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对于金融诈骗罪进行实质性的把握,从而将那些不需要刑法规制的金融诈骗行为排除在犯罪圈之外,这不仅是对金融领域特殊性的尊重,也是确保金融行业能够良好发展的保障。这种限缩首先体现在欺诈程度方面的限制性要求。具体而言,任何诈骗罪的成立都需要一定的欺诈程度,否则该行为难以称之为诈骗行为,但是不同类型的诈骗罪对于欺诈程度的要求不尽相同,相较于诈骗罪而言,金融诈骗罪在欺诈程度上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与标准。
(一)市场经济对于一定程度的欺诈有容忍义务
从伦理角度看,“诈骗”是一种与道德变迁息息相关的规范判断,随着道德的宽松化而逐渐萎缩。一个原始部落视为“欺诈”的卑鄙行为,在现代社会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交往必需。从社会角度看,欺诈是人类交往的润滑剂,无谎言不文明,不掩饰无礼仪。[[v]]欺诈行为的这种历史变迁,主要呈现在以下两个层面:首先,从纵向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欺诈的容忍态度逐渐趋于缓和。“真实的谎言”难言褒贬,“善意的欺骗”难言对错,文明不断溶解着欺诈,公众不断包容着诈骗,“欺诈”在现代社会正变得司空见惯。[[vi]]人类历史的发展脉络表明,早期社会单一的价值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的社会生活,原始社会对于是非善恶的简单评判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早已可遇而不可求。曾经崇尚诚实信用的熟人社会被日益频繁的人口流动所冲击,进而加剧了彼此间的距离感,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交往中的一些欺诈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其次,从横向维度来说,不同领域对于欺诈的容忍程度也日渐呈现分化之势。经济活动以追逐利润为根本,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尔虞我诈,俗话说无奸不商,以传统思维中欺诈程度的认定标准来衡量金融领域的欺诈行为无疑是不公平的。尤其是金融领域本身即具有一定的博弈属性,对于市场信息的掌握程度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一个市场主体能否在竞争与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有自身的运作机制,能够对一定程度的欺诈予以消解,缓和欺诈行为对于金融秩序的冲击,进行自我修复,因而其对于一定程度的欺诈有容忍义务。这种容忍义务与金融领域的本性不可分离,使得生活领域与金融领域对于何谓欺诈有着不同的认识,进而对于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欺诈程度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与认定标准。
(二)特殊主体对于一定程度的欺诈有审查义务
就金融活动本身而言,由于投资与交易的日常化与高频率,如果刑法像对待生活领域的诈骗犯罪一样频繁介入金融诈骗犯罪,客观上既不可能,也不合理。市场主体本身的注意义务远远高于生活领域的普通民众,其注意能力也远远超过普通民众。[[vii]]参与金融活动的特殊主体多属专业人士,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通晓一定的专业技能,对于自己进行的经济行为有一定的风险预判与衡量,这就要求特殊主体恪守审查义务。这种审查义务并非强加于特殊主体的无理要求,而是特定领域参与者的准入门槛,换言之,对于那些罔顾自身利益,存在严重过错而致财产损失的被害人,理应承担由于自身过错所致的部分责任,而并非将所有责任全部推卸于实施欺诈行为的一方当事人。参与金融活动的特殊主体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刑法既非冒险投资者的守卫者,也非鲁莽经济人的保护神,没有义务为他们的过错买单,也没有责任为他们的行为背书。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淘汰机制,金融活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风险博弈的斗兽场,在这个市场化的博弈过程中,不可避免有一部分人要掉队,同时再补充一批新的成员。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规律,也是金融行业的运行规则。运用刑法的手段,对金融行业进行严格管制,与其说是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倒不如说是对经济活力的扼杀与毁灭。金融市场风险与利益共存,市场参与者有义务估量风险大小,再做出谨慎投资。[[viii]]特殊主体的审查义务,使得金融领域的欺诈程度要求更高,这种欺诈程度需要进行专业的判断,而非普罗大众的一般认知,即使是一般人看来属于欺诈的行为,在金融领域也未必达到一定的欺诈程度。
(三)刑法规范对于一定程度的欺诈应保持谦抑
所谓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因此,刑法的谦抑性具有限制机能,在现代法治社会,这是刑法应有的价值内涵。[[ix]]谦抑性要求刑法的适用需谨慎、克制,就社会关系的调整而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刑法的介入程度也有所差别。在生活领域之中,人们彼此之间特别重视人际关系的交往,相互之间的信赖关系被赋予重要意义,因而需要刑法介入其中,多加关照,给予保障,因而对于刑法的依仗程度更高。相反,在金融领域之中,一定程度的欺诈可以说是一种商业策略,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商人使用某种程度的夸张用语,宣传其商品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这种行为只要是作为交易习惯,在经济活动所允许的范畴之中,就不能说是欺骗。[[x]]因而,刑法规范不宜过分介入金融领域。与此同时,与其他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相比,刑法是法律规范战线上的最后一座堡垒,是以一种保障法的地位而存在的。在对金融领域的诈骗行为进行调整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民事法律规范与行政法律规范的作用,通过前置法可以妥善处理的问题,不必动用刑法来解决,这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尤其是针对我国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较晚,发展不够成熟,因此需要给予充分的时间来使其成长、完善。对于在金融领域中的一些不规范,甚至逾越法律边界的行为,不应该过早的以刑法保护之名行干涉扼杀之实。故此,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就要坚持在欺诈程度的问题上生活领域与金融领域的不同认定,质言之,就是在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之间树立差异性的欺诈程度认定标准。
三、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解读
非法占有目的乃是诈骗类犯罪成立所必备的构成要件,然而,在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具体含义是否相同,其认定的方式与判断的过程又能否一致,这是一个值得进行研究的问题。在笔者看来,以往的研究只关注金融诈骗罪是否需要非法占有目的以及如何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但对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要素在两类犯罪之间扮演的角色并未给予过多关注,忽视了非法占有目的在不同犯罪之中的不同内容。实际上,金融诈骗罪之中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在表述上与诈骗罪无异,但若考虑到金融领域的价值取向以及刑法的谦抑性,则会发现在同样的表述之下,金融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与把握上与诈骗罪存在差异。
(一)事实层面上金融诈骗行为存在权利外观
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划分刑事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重要分界线,但实际上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与认定,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并不完全相同。对于金融诈骗罪而言,由于其从事一定的金融活动,具备一定的权利外观,因此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更为严格。以贷款诈骗罪为例,即使行为人实施了某种欺诈行为从金融机构获取一定得贷款,但其后投入生产经营,有效的贷款合同赋予行为人以权利外观,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占有并使用资金存在合法有效的权利基础,岂能说行为人具备了本罪所要求的非法占有目的。我国亦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尤其是在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非法获取资金,若获利后马上归还资金,则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很明显。[[xi]]对于诈骗罪则不然,倘若行为人实施欺诈手段获取了对方的财物,即可认定具备了非法占有的目的,进而可以按诈骗罪论处,行为人事后还款与否改变不了犯罪既遂的事实。由此可见,权利外观的存在使得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与判断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诈骗罪而言,通过转移财物的客观事实即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而对于金融诈骗罪来说,则需要更多的事实才能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二)法律层面上非法占有目的具有明文限定
金融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有别于诈骗罪不仅在于权利外观的存在与否,也在于司法机关的明文规定。为了准确把握金融诈骗罪的适用,最高法院曾于2001年颁布《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在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设置了更严的标准。根据《纪要》的规定,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通过这一表述,我们不难发现,司法机关认为对于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可以,即实施诈骗行为 + 资金不能归还 + 特定情形要求。相比之下,关于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则不存在诸多的限制与附加的条件,根据行为人客观上转移财物的事实即可推定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由此可见,虽然同为非法占有目的的表述,但在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之间,该目的认定的标准并不相同。
正确认识金融犯罪的必然性,有利于制定合理有效的防治策略。[[xii]]就金融诈骗罪而言,与其持仗刑法之剑来对金融领域、金融行业强行干预,以求肃清金融犯罪,莫不如完善金融监管体系,设置市场准入机制防范于未然。将全部力量放置于事后的重处以求规范金融市场,实际上乃是本末倒置之法,也有违金融领域的价值取向与刑法谦抑性的基本要求。因此,有必要在金融诈骗罪的适用上,坚持在欺诈程度与非法占有目的上予以限缩性的解读,将其作为限制刑法在金融领域扩张的缓冲区与隔离带。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论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2):20
[[1]] 参见高艳东.金融诈骗罪立法定位与价值取向[J].现代法学,2003(3):144
[[1]] 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40—341
[[1]] 刘宪权.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J].政治与法律.2017(4):28
[[1]] [英]马林诺夫斯基、塞林.犯罪.社会与文化[M].许某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31
[[1]] 李赪.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认定标准差异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73
[[1]] 蔡道通.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以金融诈骗罪行为类型的意义为分析视角[J].法学家.2015(5):33
[[1]] 任燕珠.论转型社会背景下金融犯罪刑罚观念的调整[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3):75
[[1]] 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6
[[1]] 黎宏.日本刑法精义(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432
[[1]] 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39—440
[[1]] 黄伟明、李涛.从金融视角看金融犯罪[A].张智辉、刘远.金融犯罪和金融刑法新论[C].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4
扫二维码用手机看
相关新闻
更多>>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111号济南华润中心55-57层
邮编:250014
电话:0531-66590815
传真:0531-66590906
邮箱:zhongchenglawyer@163.com
众成清泰(济南)律师事务所 鲁ICP备05025561号